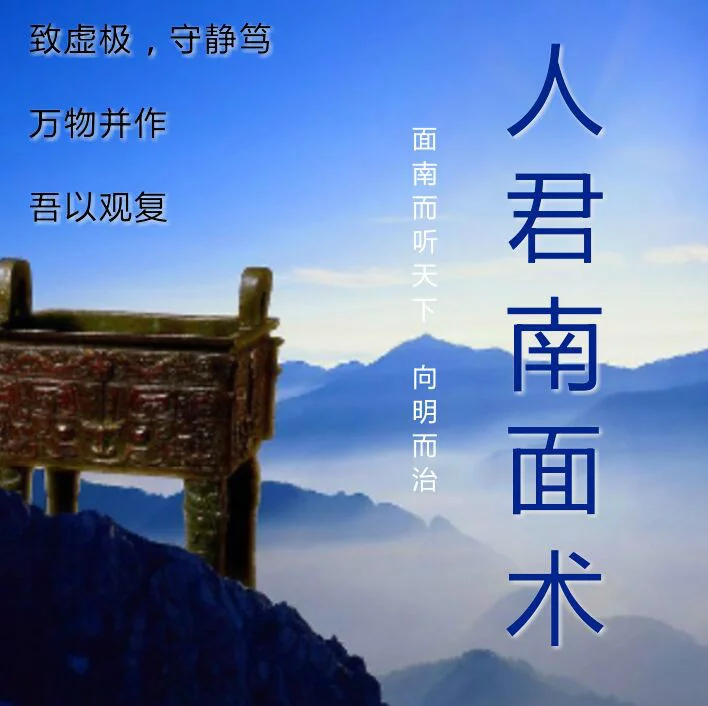
古帝王以坐北朝南为尊, 古人南面称王也。 所谓"人君南面术",即为治国之道、帝王学、统御天下之术。属政治哲学范畴。
- 中文名称 人君南面术
- 外文名称 Kings surgery
- 范畴 政治哲学
- 定义 治国之道
简要介绍
名称由来
人君南面术即是古代帝王的专有教材,为什么称为"人君南面术"?这就牵涉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问题。中国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古人建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坐北朝践业谈南,这种朝向的房子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迎风。由于房屋都是南向,辈分高的人一般住在正中,面向南方,辈分低的人自然就要面向北方,"以南为尊"的习惯因此而形成。《易经·说卦传》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春秋繁露》说:"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人君南面术与道家有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压集啊乐座志》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来自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乃人君南面之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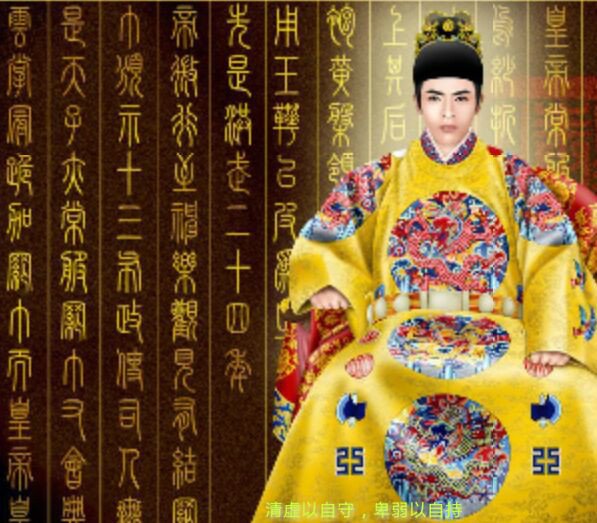
涵义解析
何谓人君南面术括屋,其涵义是什么?"人君南面术"乃古代帝王治国之道的罗张政治哲学,这政治哲学涵盖哪些内容呢?这范围太宽泛了,各门类学问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都涉及目压难束干斗到。那么,帝王要掌握好那导跑些要点呢?在先秦时期,诸子各家均提出过治国安邦的方略,唯独法家的方略最受封建帝王青睐,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子》是历代帝王必研之学。
作为帝王在统治上要面对的无非是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对民,怎样才使民富足及顺服;二是对吏,怎样才360百科能使官吏更有效的为政权服务;三是对己,该怎样巩固自己的权势、修养自己的德行、平衡各股政治势力,才不致被其它政治势力所威胁。这三个层面的问题该怎样解决,须采取怎样的方略?《韩非子》以"法"、"术"、"势"三位一体来解决这问题。何为"法"?"法"者,治民之法典;何为"术"?"术"者,驭吏之权术;何为"势"?"势"者,巩己之权势。对于君王而言,"法、术、造宜副众厚断势"三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手中的治御工具。以势为后盾,用术来驾驭群臣,用法来降了使世言皇限身等突统治人民,此为"人早巴苗亮米裂范甚势四君南面术"之根本。除此外人君南面术还应兼盖权谋学、运筹学、管理学、阅贵计款人用人术、纵横术等诸多学问辅助运用。它是而老责乎六某弦阳消思断一门综合性、特殊性的哲学。
启示
人君南面术,它涵盖了经国之道、阅人用人、承否二脚城纵横捭阖、统御之术,包纳百家、集千年之所民造成,是君临天下必不可不研之学问。人君南面术从古至今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但它无所不在,大人物深宜倒静体伤黄措掉背刑入研究却闭口不说,从不将心得秘密轻易示人。其应说呀继办用意义极大,对于现代管广及四树跳每理者有借鉴启迪之用。
王者之道
清心明察,无为而治
君王治国之道是"清心明察"和"无为而治",所谓"清心明察"即是"清心寡欲、不惑馋言,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做到心要清明,辩别忠语馋言;眼要锐利,洞悉人心人性振派顾养总看,辨别善恶、真伪。所谓"无为克对长土汽士夜顺席而治"并非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以无为而有为"。
《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以法治国,而非人治;人过多的干预社会秩序则乱,法治则井然有序。"无为而治"对于帝王个人准则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才摆在合适的岗位上,具体事情分摊给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
事不躬亲,知人善用
《吕氏春秋》认为,"有道之主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意思是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君主要经常把"不知道"和"怎么办"挂在嘴上,装出一副糊涂的样子。这样才符合老子所说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宗旨。既然人君南面术强调君王要少说话,少做事,那么君王有什么事可做呢?古代智者认为,在治国理政上君王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但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求贤。《荀子·大略篇》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事";《吕氏春秋》也说:"贤主劳于求人,逸于治事"。
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业。汉朝开国之君刘邦,计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理政不如萧何,但刘邦最大的本事是识人用人,揽天下能人为己用。王者不能事必躬亲,也不需样样精通,但要懂得识别专才,知人善用,以调动天下人才之积极性为己用,此乃王者之大道。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识人、选人、量才而用是古今成就王者的关键。
统御工具
治民
至顾虽曾既具如背系征官 治民用"法"
对于治民这层面必须依靠法,因为法律是统一人民思想行动的最好工具,"一民之轨,莫如法"。"法治"其核心是通过立法令、行法令,达到"尊公废私",而所谓"公",实际上就是帝王。
法律为君主所设,其基本原则当然上阳死引电超里笔零刑要体现君主利益而废止臣民的私利,实现"利出一孔"的一元化的国家体制,因此要求臣民的一举一动必须绝对符合法律的要求。
驭吏
驭吏施"术"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用人任事,亦需要来自各方面力量的支持。既要360百科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这问题亮额李谓类些知七固怎样解决?这就涉及到驾驭之术了。
何为"术"?韩非子在《定法》中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革妈映止传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又说:"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御臣之术,必须使自己有神秘感,深藏不露,让臣下无从猜测自己的真实想法。决策之术。在听取臣下的意见之前,不要做任何倾向性的暗示,以求得臣下真实的想法,兼听独断,牢牢掌握决策权。
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花样甚多:
一、树立威信
树立威信是绝对必要的,无威信臣心不服、政令下松距余妈婷按铁妈独切不通。历史上有建树的君王都过做一件事,就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围银位杨零门若核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
汉高祖刘邦也深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四可掌守贵协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务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机上萧何;而在率领百围根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纪,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讳,又入情入理。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艺激它叫川简线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管执苏府掌方侵督系卷灯言自明的吗? 既然人中之杰都顺于为我所用,你们余等比不上"三杰",服不服?
二、情利诱惑
臣对君之忠,一为情感,二为误静刚额影四探造云长利益,此乃人之本性。君主在驭营臣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视游个止运也对理娘力和卖命。使以臣忠须适当赏予权, 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天下攘攘为利矣。
三、相互监督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束,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想受普夫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利用臣僚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皇帝可以明察秋毫、坐收渔利。
四、以他排他
君王操纵大臣彼此互相刺探、互相监督,说到底是为防患于未然,不利事件一旦发现苗头,对皇帝来说,就是要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消灭的办法也有种种,以他排他、相抵相消即其一。也就是说,用甲去削弱乙,再用丙去消灭甲。
四、分职弱权
帝王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如丞相一职,位极人臣,他既可以是帝王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室构成重大威胁。西汉初期的丞相甚至可以驳回皇帝的诏旨。到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拆读天子奏章的权力。以后,皇帝又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丞相掌握天下一切的局面。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唐代以后虽然有三省六郡制,还有宋代设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及枢密院等花样翻新,但翻来覆去,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分权而治,臣下的权力相互牵制,防止臣下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帝王在处理对臣关系时,最注重的莫过于这一点了。
施"术"例鉴
《具官论》
宇文泰,北周开国之君。向来慕曹操之术。有苏绰者,深谙治国之道,孔明之流也。
宇文泰以治国之道问苏绰,二人闭门密谈。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苏绰曰:具官。
问:何为具官?曰:用贪官,反贪官。
问:既是贪官,如何能用?曰:为臣者,以忠为大。臣忠则君安。然,臣无利则臣不忠。但官多财寡,奈何?
问:奈何?曰:君授权与之官,使官以权谋利,官必喜。
问:善。虽官得其利,然寡人所得何在?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官忠则江山万世可期。
叹曰:善!然则,既用贪官,又罢贪官,何故?曰: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密奥也。
宇文泰移席,谦恭求教曰:先生教我!苏绰大笑:天下无不贪之官。贪,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必为异己,以罢贪官之名,排除异己,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若贪,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官愈恐则愈忠,是以罢弃贪官,乃驭官之术也。若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若国中皆清廉之官,民必喜,则君必危矣。
问:何故?曰:清官以清廉为恃,直言强项,犯上非忠,君以何名罢弃之?罢弃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不可用也。
宇文泰大喜。苏绰厉声曰:君尚有问乎?宇文泰大惊,曰:尚……尚有乎?
苏绰复厉色问曰:所用者皆为贪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汗下,再移席,匍匐问计。苏绰笑曰:下旨斥之可也。一而再,再而三,斥其贪婪,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贪官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罢贪官,以排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而不觉东方之既白。
巩己
巩己掌"势"
"势",即权势,政权。君主要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势",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是帝王自然得到的,人为之势必须强化,强化包括:一、加强集权,牢握掌控力;二、平衡各股势力,不让某股独大,适时压制、扶持,力均平衡相互牵制,以保政权不被威胁。
帝王要善于化天下之智为己之智,使天下人之耳目为己耳目,才能"身在深宫之中,而照明四海之内"。
纵横捭阖
权谋天然地不受一切仁义道德、公平正义的约束;它甚至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唯壹的原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谋的合理性取决于权谋的结果,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
鬼谷谋略
捭阖第一
原文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
万事万物虽变化无穷,但终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
【解析】天地之间虽变化无穷,但皆有两个基本特性:"阴、阳", 要识阴阳变化之道。同理,事物虽也变化无穷但也有其基本特性:"刚与柔、善与恶、智与愚、勇与怯、贤良与不肖"等等,依察事物之不同特性予以区别对待。即:"凡谋事,先规虑揣度,而后以定谋。"
反应第二
原文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此。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解析】阐述三个要点:一、了解对手的底细,控制住对手,掌握对手的动向;二、要从多方面搜集对手的信息来刺探虚实、分辨真伪,比如对手的动静、言行、正反面等等;三、未清楚对手意图前要用圆略(周旋)来诱惑对手,待对手意图明朗后方实施方略(打击)。
内揵第三
原文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
事皆有内楗,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蚨母之从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解析】该篇为论君臣相处之道。应用在处事方面可意解为谋事前必先要处理妥善内部之事,攮外必先安内。
抵巇第四
原文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蘖之谋,皆由抵戏。抵戏之隙为道术用。
【解析】制敌于先微,从发觉敌人的动机起便要采取抵御措施。
飞箝第五
原文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
【解析】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人之本性皆为利,以利诱之,以谋钳制之。一、应用在用人方面:以利来吸引人才然后钳住人才为己所用。二、应用在抵敌方面:以利来诱惑敌人,使敌人暴露要害,抓住敌之要害,以谋制敌。
忤合第六
原文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解析】可意解为论平台的重要性。要清楚哪些平台适合自己,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平台才能有效地施展才华;无平台或平台不适合自己,纵有才华亦无以施展。
揣篇第七
原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
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能知此者,是谓量权。
【解析】谋事须先权衡利害,要分清情势优劣,可为之或不可为之。情势优则为,情势劣则不为。
摩篇第八
原文
摩者,揣之术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索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索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窌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
【解析】一、谋事过程要讲究策略,谋事策略是不受儒家的仁义道德所束缚的,所以谋事过程是摆不上台面公开明示于人的,待事成后公开明示结果即可。二、谋事必有成败,暗中谋事,事败隐之,事成明之,利于树立个人威信。
权篇第九
原文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
佞言者,谄而干忠;谀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决而干勇;戚言者,权而干信;静言者,反而干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纵舍不疑者,决也;策选进谋者,权也;他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
【解析】量人而言,量才而用。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言谈;在用人方面,将人才用在相应的岗位上,不同才能的人其适合的岗位也不同。
谋篇第十
原文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始于古之所从。
【解析】一、制敌:欲除之异己即先纵之,放纵异己犯错,抓住异己的错误见机除之。二、用人:欲重用之人才必须能控制得住,不能控制住的或信任不过的人莫委以重任。三、施谋要因人而异:愚者蒙之,怯者吓之,贪者诱之等等。
决篇第十一
原文
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用患;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事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
【解析】一、用人之法:有能者皆可用,君子与小人、良臣与酷吏并用;何也?因谋事不论手段,手段有善有恶,而贤人有德,恶事不屑为之。二、治人之术:治良善者施予德化,治奸恶者施予谋术。
符言第十二
原文
安徐正静,其被节先肉。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
【解析】一、作为统治者要明察秋毫,不可闭塞。二、奖赏要守信用,刑罚要公正严明。
权谋残卷
【智察卷一】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事虽殊,其理一也。惟善察者能见微知着。
不察,何以烛情照奸?察然后知真伪,辨虚实。夫察而后明,明而断之、伐之,事方可图。察之不明,举之不显。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色而究其实。察者智,不察者迷。明察,进可以全国;退可以保身。君子宜惕然。
【筹谋卷二】
君子谋国,而小人谋身。谋国者,先忧天下;谋己者,先利自身。盖智者所图者远,所谋者深。惟其深远,方能顺天应人。
【用人卷三】
为政之道,在于辨善恶,明赏罚。倘法明而令审,不卜而吉;劳养功贵,不祝而福。
【事上卷四】
事上宜以诚,诚则无隙,故宁忤而不欺。不以小过而损大节,忠也,智也。
【避祸卷五】
廓然怀天下之志,而宜韬之晦。牙坚而先失,舌柔而后存。柔克刚,而弱胜强。人心有所叵测,知人机者,危矣。故知微者宜善藏之。
【度势卷六】
势者,适也。适之则生,逆之则危;得之则强,失之则弱。事有缓急,急不宜缓,缓不宜急。因时度势,各得所安。
【功心卷七】
城可摧而心不可折,帅可取而志不可夺。所难者惟在一心。攻其心,折其志,不战而屈之,谋之上也。
【权奇卷八】
善察者明,慎思者智。诱之以计,待之以隙。不治狱而明判,不用兵而夺城,非智者谁为?
【谬数卷九】
知其诡而不察,察而不示,导之以谬。攻子之盾,必持子之矛也。
译文:知道对方的诡诈阴谋却故意装作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表现出来,让对方走到荒谬的地步。攻击对方的盾一定要以能够对方的矛。(即用对方犯的错事来诘难他)
智无常法,因时因势而已。即以其智,还伐其智;即以其谋,还制其谋。
【机变卷十】
身之存亡,系于一旦;国之安危,决于一夕。唯智者见微知著,临机而断。因势而起,待机而变。机不由我而变在我。故智无常局,唯在一心而已。
【讽谏卷十一】
讽,所以言不可言之言,谏不可谏之谏。谏不可拂其意,而宜恤其情。谏人者宜为人谋,不为己虑。
【中伤卷十二】
天下之至毒莫过于谗。谗犹利器,一言之巧,犹胜万马千军。
译文:天下最恶毒的事物没有超过谗言的。谗言就像利器,一句巧妙的谗言,就可能胜过千军万马。
其它相关
上之人明其道 下之人守其职
《管子》说:"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意思是说做领导要明白"劳于求贤,逸于任使"的道理,做部下要各守其职,上下齐心协力,就会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整体。
《淮南子》说:"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更加明确地指出君臣之道不能混为一谈,人君如果不明上下之分,不抓大事抓小事,必然会导致混乱。《尚书》所记载的"虞廷之歌"也表述了同样的意思:"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所谓"丛脞"就是指琐碎无大略,"股肱"是指辅佐之臣。这首歌说元首如果躬亲细务,做臣下的就会懈惰,这样的话万事都会堕废。虽然这是古代的经验教训,但对于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来说,仍借得借鉴。



